kaiyun官方网app下载app 为了一个人的直立行走
今年46岁的李华是湖南省杞阳县磐石镇人,他的愿望很简单:想见见妈妈的面,虽然妈妈每天都在他身边。
但他无法抬起头。
他的头抵着胸口,胸口抵着肚子,脸抵着大腿,整个身体就像一把折叠刀。
第一眼看到李华时,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科主任陶惠仁弯下腰,全队队员都从各自的角度尽力看清李华的全貌,但没有人能看清楚。
他们看不到李华的全脸。
李华是全球报道的脊柱后凸畸形最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像李华这样头部折向大腿的病例,无论在国内外都极为罕见。”陶惠仁说,迄今为止,国外文献记载的脊柱后凸畸形最严重的病例是一名韩国男孩,他的头部折向距离大腿二十多厘米。
“无法用现有的医学术语来定义。”陶惠仁多年来每年做300多例脊柱侧弯手术,累计近万例。陶惠仁及其团队只能用一个中英文组合词来定义这个病例——“3-on折叠人”,即下巴靠胸骨、胸骨靠耻骨、脸靠股骨(下颌靠近胸骨、胸骨靠近耻骨、脸靠近股骨)。
他这样折叠了整整28年。
一般咨询
第一次见到李华时,曾参与过中国首例换脸手术、经历过不少疑难病例的孙燕燕就知道,这将是她30年麻醉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手术。“这不仅是对我和我的团队的挑战,也是对全世界麻醉医生的挑战。”
对于整个医院来说,这也是脊柱病科的珠穆朗玛峰。2019年8月14日,第一次术前专家会诊举行,全院领导、11个科室负责人到场。主席台上,陶惠仁用一页又一页的PPT向大家讲解李华的病情。
放射科吴光耀主任首先发言。由于李华身体处于折叠状态,放射科无法进行核磁共振扫描和双能量骨密度仪检查,人体很多细节无法清晰显示。凭借多年临床经验,吴光耀表示:“虽然患者内脏、血管等结构不清晰,但总体来看,没有大的异常。”不过kaiyun体育,“从CT表现来看,患者骨质疏松严重,需关注术中内固定握持力、抗炎治疗,以及术后内脏系统应激反应等。”
呼吸科主任任新玲介绍,患者口唇发紫,平时活动不多,几乎不使用肺储备功能,身体折叠导致胸腔和肺部长期受压,肺活动受限,应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肺功能基本可以耐受手术。但“应注意围手术期肺部管理,避免发生肺炎”。
心脏内科主任李海英认为,由于患者体位受限,超声扫描只能看到患者心脏的部分区域。“患者心脏及大血管承受压力大,手术复杂耗时长,术中还存在循环衰竭、心律失常等并发症的可能。心脏内科团队随时准备提供强有力的心脏支持。”
很快,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麻醉科主任孙燕燕的身上。
“首先不能用局麻,因为创伤太大,病人椎间隙太窄,椎管内麻醉也不行,神经阻滞没有效果,而且如果局麻药进入血液,引起抽搐或者呼吸困难,李华就有生命危险!我们只能用全麻,插不进导管,不但手术没法做,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因为麻醉面罩不能完全插进去,一旦身体反应严重,呼吸、循环系统就控制不了,就没有心肺复苏和抢救的机会了。”
孙燕燕说完之后,全场顿时安静了五秒,大家都知道,这次手术只能成功,如果失败,就没有恢复的机会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巨大考验,手术的第一步就是麻醉。
在李华面前,常用的面罩、喉镜、喉罩等麻醉设备和方法都派不上用场。在国外,对于像这样的严重困难气道,麻醉医生往往会放弃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保证供氧。但即使选择这样昂贵、复杂、创伤性大的方法,对李华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股静脉和颈静脉也被堵塞,无法放置体外循环导管。
清醒气管插管只能使用纤维支气管镜进行。“因为纤维支气管镜是一种可以弯曲和调整角度的软镜,所以可以在探查时向前移动。”
清醒插管对患者刺激大、不适感强,一旦诱发喉痉挛或呼吸抑制,对李华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患者必须保持清醒、呼吸安全,患者也必须稳定、舒适。只有表面麻醉充分、镇静非常精准,才能避免过度刺激,实现成功插管。
“你确定你会成功吗?”
“没有,但我愿意尝试一下。”
会后,孙燕燕坦言,自己愿意尝试,一是同情李华,“他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存状况都令人担忧”;二是对同事的信任,“我知道有风险,但我们没有退路,如果做不到,后面的所有可能就都没了。”
经过反复讨论,方案最终敲定。“我们只能把他的股骨、颈椎、胸椎、腰椎逐一打断,再把整个脊椎拉直、固定,完成骨骼重塑,这样才能把脊椎拉直,重新打开李华完全折叠起来的身体。”陶惠仁说。
病史
李华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剧痛是在他10岁那年。“我的右脚关节疼痛,一直蔓延到膝盖,然后膝盖流出黄色液体。”他赶紧到医院,医生把肿胀的膝盖封好,再把黄色液体抽出来。膝盖和脚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李华觉得自己的病好了。
没想到,8年后,同样的疼痛症状又出现在另一只脚上,从脚掌一直延伸到膝盖。李华再次到医院就诊,接受了同样的治疗方案,但疼痛感并没有像8年前那样消失。
很快,他的腰就无力了;随后,他必须用手压着臀部才能勉强走路;再后来,他睡觉时髋关节的疼痛就会把他惊醒,他无法平躺,只能侧卧。
他看了很多医生,医生都说是关节炎。他问医生为什么疼痛在不同关节处不断变化。一位医生回答说:“这叫游走性关节炎。”
后来,李华因为疼痛只能弯着腰走路,没过多久,李华的脖子也开始弯曲。
这个农村家庭,能借到钱就去看病,借不到钱就不去看病。因为病情复杂,无医可治,李华就学会了用感冒药来止痛,这“便宜又管用”。
直到这一天到来——整个人的脊背长成了难以形容的弓,脖子越来越弯,直至脸贴在大腿上,两者再也无法分开。

手术前的李华
中午吃得很少,很吃力,晚上因为胃部受压无法进食,开始营养不良,骨质疏松严重,心肺功能也不好,走路双腿无力,拄拐杖容易摔倒,只能借助小凳子行走。
2018年的一天,吃了感冒药吐了很多血后,李华到大城市就医,因为手术难度太大,他再次被医院拒绝。
更麻烦的是,腹部出现了压疮。
2019年5月,夏季还未正式到来,李华已感觉到炎热,由于长期蜷缩身体,腹部、胸部长期未清洗,身体分泌的污垢堆积了大量,形成的压疮开始散发出恶臭。
褥疮带来的疼痛甚至比刚开始的关节痛和长时间蜷缩身体带来的疼痛还要强烈。“感觉皮肤被磨得很薄。”李华说。
实在等不及了,李华在母亲的陪同下,从湖南来到了深圳。
第一次手术:太空
手术的首要条件是李华的腹部压疮彻底治愈。
上药是个大工程,两个人要从前到后扶着李华,稍微将他的身体撬开,护士再用长棉签蘸药,尽量擦到溃疡处。每次,护士都要戴上好几层口罩,才能忍受褥疮的恶臭。换完药后,为了防止伤口长时间浸泡在药里,护士们还想出了用吹风机吹干伤口的办法。
同时,陶教授还要求李华每天吹气球,锻炼他的肺功能。
两个月后,李华终于获得了手术的资格。
8月15日凌晨,双侧股骨颈截骨手术开始。
手术体位成了问题,几乎所有的手术都是在卧位下进行的,如果像李华这样进行手术,颈椎没有受力,没有有效的支撑点,很容易导致关节被挤压。
护士们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她们将手术用的塑料手套装满水,但不要太饱和,并制作大小不一的流体水袋垫。水是流动的,当身体按压在上面时,压力就会向外膨胀,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U型水囊臀垫成为李华首次手术的最佳稳定器,“坐好”后,李华终于开始了第一次高难度的麻醉气管插管。
在患者清醒状态下,插管刺激性很大,所以表面麻醉和镇静必须处理得非常准确。在手术室里,孙艳艳先用鼻扩张器通过一侧鼻孔对患者鼻咽喉部进行表面麻醉,再在另一侧放置鼻咽气道进行高流量通气。同时采用滴定法泵入药物,减轻患者插管刺激。
手术前,孙燕燕与李华对话四次,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放心,我会尽力的。”“我没有告诉他会有什么危险,只是告诉他要相信我,清醒的时候要听我的吩咐。”
当这根比食指还粗的管子插入李华左鼻孔时,“每向前移动一点,我都会和他沟通,让他深呼吸,抵抗不适。”当孙燕燕成功找到声门,将管子插入气管时,整个手术室都欢呼起来。
李华71岁的母亲唐东晨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她眼含热泪地说,手术会很痛,但是他已经受了20多年的苦,这点痛不算什么。
她从40多岁开始带李华去医院治病,农闲时就给李华做饭挣点钱。李华病情越来越重,她已经不能出门了。她每天给李华擦身、喂饭、清理粪便,把他当成宝贝一样照顾。家里的旧债还没还清,新债又来了。
在妈妈眼里,李华是个很乖的孩子kaiyun官方网app下载app,十岁就能自己做饭,学习成绩也不错,每天放学后还帮家里割草、烧柴。妈妈心里很可怜他,“他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第二次手术:抬头手术
第一次手术后,李华的脸部与股骨之间第一次有了间隙,但让陶教授遗憾的是,他的双腿仍然没有足够的空间张开,头部也还很低,下次手术仍然会非常困难。
现有的整体方案必须修改kaiyun体育,原来的手术方案是把颈椎截骨手术放在最后做,因为这个手术危险性最大,相当于在颈椎脊髓上做手术,从脑部延伸到全身的神经都要经过这里,如果不小心伤到,轻则瘫痪,重则有生命危险。
但现在,最后一项手术必须提前做完。
“整个手术过程中,最困难的其实是制定手术策略。”陶惠仁那段时间“特别焦虑”,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深夜。
陶惠仁犹豫了很久才接李华的手术,因为风险太大。看到李华发来的病历时,他第一步就是找到孙燕燕,商量麻醉的可能性。孙燕燕说:“你做,我也做。”
最后他告诉李华,如果李华愿意接受挑战,就来深圳,他会尽全力去完成,此时医院也表示支持。
分管医疗的副院长宫鹏教授参与了两次MDT(多学科联合诊疗),他说,李华的三折病例,是脊柱骨病的珠穆朗玛峰,在一个被病魔折磨了28年、即将用尽生命最后一丝光辉的人面前,名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希望这样的人几个月后能够有尊严地走出我们医院的大门。”龚鹏在会上说。
第一次手术后,陶惠仁教授走下手术台时疲惫不堪,但他边走边给妻子打电话。“我妻子是心脏科医生,第一次手术时,我发现病人心率有点快,就跟她讨论是什么原因。”后来,陶教授的妻子告诉他,可能是失血过多导致的。第二次手术时,陶教授输了更多血,心率果然降了下来。
第二次手术,陶惠仁决定先矫正李华的颈椎后凸畸形,让李华能够抬起头、平视前方。
除了颈椎手术容易危及脑部及全身神经之外,颈椎矫正的程度更是要求精准,多一度李华的眼睛就看不清天空,少一度又看不清远处。手术究竟该在哪个部位进行?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麻醉仍是绕不开的难题。第一次手术时插管成功,但后续困难接踵而至。由于李华长期处于受限体位,心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1/3。手术创伤性极大,术中血流动力学波动剧烈,一旦发生心跳骤停,根本没有胸外按压的机会。麻醉团队最终在全麻基础上采用骶管阻滞。
幸好,第二次手术非常成功,陶惠仁最终对李华的第七颈椎实施了截骨手术,并将第四颈椎与第四胸椎融合,矫正了罕见的颈椎畸形,让“断头台”重新回归。
手术后,李华神志清醒地走出手术室。28年来,他第一次能抬头看人,别人也能看清他。他抬头看人的第一反应是愣住,然后笑,一直笑个不停。
他转过身,朝着医生微笑着竖起了大拇指,孙燕燕第一次看清他的脸,开心的说道:“没想到你看上去这么年轻,真是个帅哥啊!”
28年后,他终于要再次见到母亲的面容了,他有些害羞,甚至有些不敢看母亲,心情很复杂。
他说,那一刻,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怪感觉,“我能想象妈妈会变老,但她怎么会老到我都认不出她了。”
回到病房,李华28年来第一次看电视。当晚看完中国男篮对阵波兰“瑶头探奇”队的比赛直播后,他说:“幸福已经停止了。”
妈妈唐东辰不停地擦着眼泪,“我现在能抬起头了,吃饭也没那么难了。”
第三次手术:平躺
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前两次手术,李华的股骨和颈椎分别被打断,这一次,要打断胸椎和腰椎,然后还要把整个脊椎拉直固定,重新塑形,才能把脊椎拉直,手术一个接一个,不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2019年9月18日,全院参与的第三阶段手术开始,这是让李华躺下的关键一步。
最困难的是找到脊柱弯曲最大的两个地方。
手术前,陶惠仁带领脊柱外科医师段春光等队员多次演练、反复确定手术方案,初步决定将弯曲最为严重的第12胸椎和第3腰椎打断,再重新连成直线,让第8胸椎至第5腰椎融合。
这次手术和以往任何一次手术一样复杂,截骨后患者要从“膝胸俯卧位”转为真正的俯卧位,“这对医生和护理团队都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其他困难也接踵而至。如何解决患者术后疼痛问题?手术中预期的出血量非常大,神经麻痹的风险极高。此外,如何在本来就复杂的解剖结构中找到可靠的深静脉,当出血量可能是体内循环血液量的2-3倍时,如何在手术过程中保持内环境的稳定?
第三台手术从当天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共计15个小时,失血量达2600毫升。团队动用了手术室几乎所有可用的监测设备,并在术中使用了针对性的液体治疗,保证了患者循环的稳定。
为了防止身体不稳定造成神经损伤,导致截瘫,几名年轻医生跪在手术台下,在无菌巾的隔离下,帮助李华稳定身体。

为了避免李华因身体不稳定,可能造成神经损伤而导致截瘫的风险,几名医生跪下来帮助李华稳定住身体。
9月18日晚10点,李华苏醒后,仰面躺着被推出手术室。
李华终于在28年的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了仰卧睡觉的感觉。然而护士发现,李华虽然是仰卧着,却不停地喊着“我要睡觉”。原来,习惯了蜷缩着睡的李华,已经不习惯仰卧了。
李华身上植入了近30枚钉子,手术后最初三天,李华只能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才能翻身、活动。脊柱骨科的护士们24小时轮流照顾他,每次进病房,护士们都会叫他“华哥”,还给他买新鞋、新裤子。
手术后,陶惠仁每天都会来看望李华好几次,“我怕他出点小问题。”
此前,陶惠仁发现,前来就诊的患者大多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身体极度弯曲,因此大多是孤身一人来到医院,缺少家庭的温暖。医护人员会一起给患者过生日,墙上贴着一张记录患者生日的表格。
“这种疾病最大的问题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陶教授说。
第四次手术:直立行走
半个月后,第四次手术即将进行,李华却突然发烧。
“那个发烧把陶主任吓坏了,他以为是感染了。”脊柱骨科护士长罗振娟回忆道。
原来,李华最后在平躺做核磁共振术前检查时感冒发烧了,后来经过一番消炎治疗,烧才退了。
罗振娟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华的情景:一辆轮椅在前面行驶,她从后面看不到轮椅里有人。当她跑到轮椅前面时,她吓了一跳——就像有人在努力蜷缩身体,弯腰挤过狭窄的隧道,却再也抬不起头来。
因为发烧,第四次手术被推迟了,陶惠仁每天要去看望李华好几次,大家都很焦急,想知道手术什么时候开始。
第四次手术为李华进行双侧髋关节置换术,让他能够站立、行走。
“如果没有迈出这一步,或者这一步不成功,李华的前三次手术都是失败的,因为衡量手术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李华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甚至能不能跑。”陶惠仁说。
该手术可预见的风险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大量出血,另外由于长期卧床,存在一侧肺局部不张、胸腔积液。
10月22日,医院召开李华第四次手术前的综合会诊,十几位科室负责人再次齐聚一堂。
感控科鲁健主任介绍,由于胸腹部长时间叠放在一起,形成死腔,易有细菌存在,甚至是多重耐药菌;短时间内连续做4次手术,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发生手术相关感染的风险极高,应积极采取措施预防。
第三次手术后,李华胸部CT显示胸腔积液,这一突发状况直接影响到手术是否需要延期。胸心胸外科主任张晓明根据胸腔积液的量、形态判断,基本可以排除脓胸,患者无明显通气障碍,可以耐受手术。
ICU(重症监护室)宋志主任也表示,经过三次手术创伤后,人体自身的应激反应会导致血常规等非特异性指标升高,而胸腔积液并不影响手术。患者卧床时间越长,病情越严重,建议手术治疗。
第四次手术,陶惠仁请来了国内著名关节外科专家吴耀平主刀,这次手术为李华身体两侧更换了人工髋关节,帮助他的双腿前后摆动,让他重新能够站立。
自2019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四次马拉松作业,共耗时38小时。
手术第二天,李华可以在别人搀扶下坐起;手术第十天,他可以独立坐起;第十五天,他可以在别人搀扶下站起。第一次下床时,陶惠仁全程在场指导,但陶惠仁还是紧张得满头大汗。
手术后,为了让李华每天坐在床上进行牵引恢复,医院专门制作了床上牵引装置,让他从最小的杠铃开始锻炼肌肉力量。
12月2日,李华紧紧握住助行器,鼓起勇气站了起来。虽然迈出一步,手臂有些发抖,双腿有些发软,但他终于迈出了46岁人生新起点的第一步。
李华的母亲站在一旁,偷偷用衣角擦拭着眼泪。
她一直保留着一张李华的照片:1991年,18岁高中毕业的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衫,双手叉腰,站得笔直。这是他患病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时,他的身高接近1.7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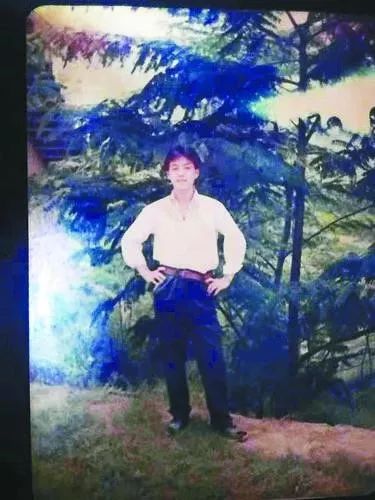
李华18岁患病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他年轻的时候想当一名军人,二十多年的人生,理想早已破灭,他只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直立行走。
在妈妈眼里,李华性格开朗,很受欢迎。邻居、朋友都喜欢和李华聊天,看不见别人的李华会静静地听,帮他们排解压力。他还给上小学的小侄女当家教。
李华的手术总共花费70多万元,四次手术花费约40万元。据李华介绍,医保可以报销近50万元,专门救治贫困家庭脊柱畸形青少年的至善慈善基金会捐款13万元,缺口还有10余万元。
李华离开湖南时带了4万多元,还交了3000元住院押金,扣除母子俩生活费等其他费用,现在身上只剩下1万多元。
李华感到很幸运,医保支付的近50万元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据记者了解,除个别地区将强直性脊柱炎列为“整形”项目不予报销外,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均已将其纳入大病医保。李华觉得,这救了自己的命。
现在,他可以慢慢地绕着10米长的病房走两圈,尽管要花一个多小时。
他很清楚,自己还要跑十米,再跑十米,再跑一米……“等2020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能站直了身子,自己走回湖南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一男
如果你喜欢,请点击这里
 鲁ICP备18019461号-4
鲁ICP备18019461号-4
我要评论